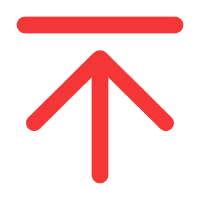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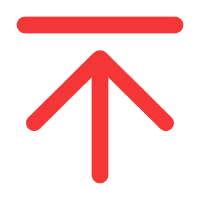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提交时间: 2024-09-03 合作期刊: 《船山学刊》
摘要:中国思想史作为一套现代意义的学科体系,初步奠基于二十世纪之初。中国思想史学科经过百年的建设和发展,一方面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为现代知识体系,并被纳入现代学科体制与教育体制,一方面确立了科学与民主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思想标准,从而推动了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化转型。但是,百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代中国学者重新撰写中国思想史,必然会面临一系列新问题的挑战。中华民族对自身文明作再反思,必须具有新的时代高度和历史深度。
分类: 哲学 >> 中国哲学 提交时间: 2024-09-03 合作期刊: 《船山学刊》
摘要:中国思想史作为一套现代意义的学科体系,初步奠基于二十世纪之初。中国思想史学科经过百年的建设和发展,一方面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为现代知识体系,并被纳入现代学科体制与教育体制,一方面确立了科学与民主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思想标准,从而推动了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化转型。但是,百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代中国学者重新撰写中国思想史,必然会面临一系列新问题的挑战。中华民族对自身文明作再反思,必须具有新的时代高度和历史深度。
分类: 历史学 >> 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提交时间: 2024-08-27 合作期刊: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摘要: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将“《春秋》始于隐”指向周平王与鲁隐公时间上的相接,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序》亦承其说,但二者仍存在很大的差异。杜预在强调时间相接的同时,亦将鲁隐公视为让国之贤君,从而将鲁隐公比之周公,对其有再兴东周的期待;但在《穀梁》的脉络下,范宁不能将鲁隐公视为贤君,而只能冀望于孔子的“将来法”。也就是说,在杜预、范宁笔下,周公、孔子产生了不同的位阶,“圣人制作”的主体也就随之改变,从而形成了“再造中兴”与“俟诸将来”两种不同的期待。究其实,则是西晋初“绍开中兴”与东晋末“礼崩乐坏”的历史现实在杜预、范宁文本中的投射,从而产生了二者对《春秋》与“圣人”的不同解读与诠释。但二者对《春秋》的解读并不仅仅是“知人论世”,更是要“知事用世”,期待《春秋》由经典文本进入历史世界,从而使现世走向《春秋》所昭示的“王道世界”。
分类: 哲学 >> 中国哲学 提交时间: 2024-08-27 合作期刊: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摘要:金岳霖《论道》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实现中西哲学的融通,建构一个既能够体现中国哲学精神传统又能吸收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之道的哲学体系。金岳霖的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元哲学,其问题意识来源于西方哲学,其论证方式来自西方哲学与逻辑学。但是,由于“道”在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及价值信仰方面居于核心地位,金岳霖建构的形而上学之道显然是立足于中国哲学的。金岳霖坚持以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哲学范畴为基础,通过一系列西方逻辑体系的论证,最终建构了一个以传统中国哲学范畴为基本框架、吸收了西方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体系。不能仅仅将金岳霖的《论道》理解为民族文化、情感归属的需求,他同时也是站在时代和人类的哲学思考高度,通过融通中西哲学以解决现代形而上学重建的问题,其形而上学之道具有回应人类普遍哲学问题的世界现代哲学意义。
分类: 哲学 >> 伦理学 提交时间: 2024-05-23 合作期刊: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摘要:“立法者是根据法则的责任的创作者,但并不总是法则的创作者”,这是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导论中提出的一个晦涩命题,学者们作出了很不相同的理解。埃里克·沃特金斯认为,康德主张上帝和人既是立法者,又是法则的创作者。这种理解是对康德命题的明显误解,没有看出康德明确否定了上帝这位立法者同时是法则的创作者。刘凤娟认为,康德主张上帝和人的立法理性作为立法者并非法则的创作者,惟有执行理性的唯一立法、在特定情境中创作具体法则的自由意志(任意)才是法则的创作者。这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康德命题的本来含义,没有看出康德命题主要是针对上帝这一立法者而提出来的,因而改变了在上帝的意志与人的理性之间的对比框架,在立法理性与执法意志的对比框架中把执行理性立法的意志当作法则的创作者。康德这一命题的本来含义应是,上帝这个立法者并非法则的创作者,我们自己的立法理性才是法则的创作者。这样理解,可以得到康德大量同主题文本的支持。康德把上帝视为立法者,表明他的立法者概念需要在其道德宗教中加以理解;他把我们自己的立法理性视为法则的创作者,则表明他在法则的创作者问题上坚持了启蒙思想原则。